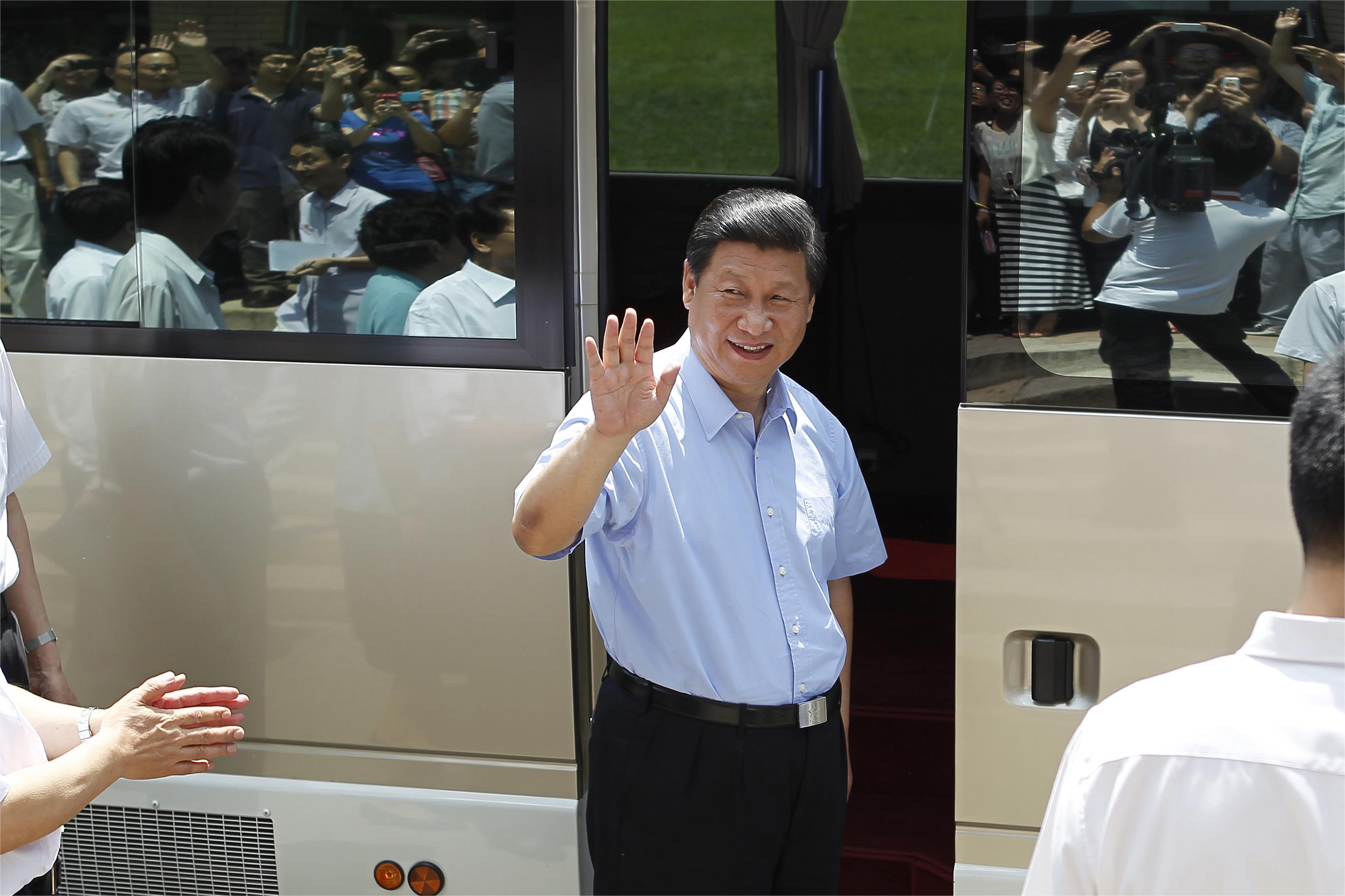你好FAST,我是你的工程师

编者按:
在宇宙的尺度下,人类弱小而微不足道,但却始终试图揭开宇宙的奥秘。 FAST,这个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世界最大单口径、最灵敏的射电望远镜始终笼罩着一层神秘的色彩,如同隔着毛玻璃观看戏剧的观众一般,公众试图努力看清这个大科学装置背后的“演员”。
2015年11月,当6根钢索拖动着重达30吨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的馈源舱(代舱)缓缓升起时,朱文白提到嗓子眼的心终于放下来了。
“那时候我觉得差不多了,这事能做成”,从国家天文台博士研究生到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馈源支撑系统总工程师,朱文白跟随着导师南仁东见证了FAST的成长。
“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茫茫宇宙中我们真是孤独的吗?人类之所以脱颖而出,从低等的生命演化成现在这样,出现了文明,就是有着一种对未知探索的精神。”南仁东生前曾说,“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想试一试。”
从1994年6月国家天文台(原北京天文台)设立大射电望远镜LT课题组,到2016年7月3日,最后一块反射面单元的吊装成功,这个创造世界射电天文界新历史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终于结束了长达22年的建设历程。
电视纪录片中,南仁东站在铺设好的圈梁上,半侧着身子望向镜头,眼中氤氲着欣慰说:“这是一个美丽的风景,科学风景。”
哲学家康德说过,世界上有两样东西能深深震撼我们的心灵:一个是心中崇高的道德准则;另一个是头顶璀璨的星空。
“感官安宁,万籁无声,美丽的宇宙太空以它的神秘和绚丽,召唤我们踏过平庸,进入到无垠的广袤。”而在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平塘县克度镇大窝凼的喀斯特洼坑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正续写着人类与星空的缘分。
但他们并不是天文学家——你好FAST,我们是你的工程师。
过去
6月初的贵州依然有些许凉意,3个半小时的车程过后,车子从贵阳市驶入平塘县克度镇,原本这条只有省道和山道的路程大约是需要颠簸七八个小时的。
渐渐地,车子驶入了一片与世隔绝的郁郁葱葱,映入眼前的洼地中,静静地伫立着一个现代机械美感与自然环境完美融合的工程奇迹。
远远望去,FAST就像一口直径500米的大锅,“锅沿”周围的“灶台边儿”上矗立着6座近百米的高塔,每座塔的上方伸出一根向中间延伸开来的钢索,拖动着一个形状不规则的白色舱室在150米的空中移动,舱室的下方是由4450块三角形面板拼合而成的“锅面”,而隐藏在“锅底”下方的数千根钢索编织成的索网,是支撑这口大锅和牵引“锅面”移动、变位的主要力量。
“苦啊,那时候条件真的很艰苦”,坐在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综合楼大厅的米色沙发上,朱文白笑着回忆起那段爬坑底,睡工棚,与蛇鼠蚁虫“殊死搏斗”的日子。
1996年朱文白硕士毕业,本着对天体物理学的热爱加入了南仁东率领的FAST团队,成为第二批参与进项目组的人,现如今早已成为团队里的“老人”,也是六塔、六索和舱构成的馈源支撑系统的总工程师。
“上个月刚刚完成了部分项目的验收,望远镜各个系统的运行也已经基本稳定了,接下来就是调整和优化的事情了。”他深深地松了一口气。
整整23年,他庆幸自己参与了项目建设的整个过程,“就像是编剧编了一幕戏剧,从创作剧本到公演,再到最后拿到奥斯卡奖的感觉。”
起初,FAST团队只有5个人,团队遵循着“小核心大外围”的发展路线,凭借着南仁东的个人魅力和四处的宣讲,吸引了20所左右高校和研究所中的近百人逐渐参与到项目的建设中来。1998年年底,FAST入选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首批重大项目,这成了真正的转折点,但机遇到来的同时,问题也随之而来。
经过多次勘测与比对,项目组最终从300多个候选洼地里面将台址选定在了贵州省平塘县大窝凼,南仁东曾说,“我们非常幸运,我们选到了地球上独一无二的,最适合FAST建设的台址。”
但台址的确定仅仅是开端,要让这个庞大的装置达到毫米级的精度殊为不易。
索网结构是FAST主动反射面的主要支撑结构,是反射面主动变位工作的关键点。索网制造与安装工程也是FAST工程的主要技术难点之一。望远镜反射面主体巨大,重达2300吨,并且要求每块反射板都可以随意变形,因此要求背后控制反射板的索网既要能够承受巨大的重量,又能够持续使用几十万次,传统的刚性结构索网显然无法满足这一要求。
“没有先例”,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南仁东和王启明坐着北上的火车,踏上了漫漫“求索”之路。“2003年的平安夜,我和南总坐了一宿的火车到了哈尔滨,白天谈事谈完了,南总又是不喜欢打扰人的性格,我俩还没吃饭就急急忙忙赶到火车站,就在秋林商店买了几个大面包啃着吃,然后又是一宿的火车回北京。”事隔十几年,所有与FAST相关的情节王启明依旧记忆犹新。
在与哈尔滨工业大学等高校的合作中,经过反复的“失败—认识—修改—完善”过程,历时一年半,团队最终完成技术攻关,制作出了能够带动面板运动的柔性钢索。
墨蓝色的工作服,少言低调的性格,再衬上常年野外作业晒出的小麦色肤色,不熟悉的人可能会误将这个FAST主动反射面系统的总工程师认作现场的工人。
但其实,那件墨蓝色的工作服是“老FAST人”身份的象征,因为年代久远,拥有且还能保持完好的人不多,最珍贵的地方是工作服的袖子上,还绣着王启明的名字。
“索网结构直径500米,整个索网共用了6670根主索、2225个主索节点和相同数量的下拉索。”王启明说,“长度11米的主索索段精度控制到1毫米以内,主索节点的位置精度达到5毫米,索构件拉伸疲劳应力幅值不能低于500Mpa。”他总是能够脱口而出与索网相关的数据并精确到个位数。
从奥运村到密云,从贵阳到平塘,“不知不觉地就走了这么多年,工期在那里,项目压力很大”。“不知不觉”是王启明反复提及的词,哪怕压力大得晚上睡不着觉,头发一茬茬地白,王启明却“几乎没犹豫过,没迷茫过,想的都是怎么解决”。自2012年圈梁等设备开始进场以来,他就成了贵州黔南地区大窝凼洼地的“常住人口”,也是那几年春节最后一个离开现场的人。
虽然“启明”二字是家中论资排辈的结果,但是冥冥中注定的缘分让王启明的一生都与FAST交缠。直到该退休的年纪,他想“该陪陪家人了”,几十年来他自觉对家人亏欠了太多,错过了孩子的成长,妻子的手术做完了他才知道。而对于FAST,这个他看着长大的“孩子”,他也知道“自己只能送上一程,是时候把接力棒交给下一代年轻人了”。
技术需要传承,王启明始终这么认为,“科学没有灰色,非黑即白。但技术不行,技术要中庸一点,要大家一起做。”
现在
现场工作总是繁杂中自有规律。
晚饭后的散步似乎已经成为团队成员固定的消遣活动,大家三三两两地谈笑着,食堂门口趴着的两条流浪狗冲着过往的熟悉面孔慵懒地摇晃着尾巴,一切静谧而美好。
每晚7点30分,100平见方的总控室里陆续站满了各个分系统的工程师,他们把每晚的例会称作“730会议”,会议汇报当天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讨论第二天的工作安排,与传统语境下冗长的工作会议不同,“730会议”通常5~10分钟便结束了。
人潮散尽,这个堪比FAST“大脑”的总控室里只留下了当晚值班的工作人员,看了一眼显示屏上的数据,一切正常,张博把身体放松在电脑桌前的座椅上。FAST团队主要是由天体物理和天文技术方法两个截然不同的专业领域的人员组成,这个爽朗的天津女孩是现场为数不多的天文学者之一。
“如果某一段电磁波突然出现大范围的波动,就说明有特殊情况,说不定是外星人的信号呢”,张博指着电脑屏幕说,“脉冲星也是在这观测到的。”原来这些惊天动地的发现诞生得如此安静。
晚上9点多,总控室里的计算机集群还在嗡嗡作响,铺满墙壁的监测画面被电子屏幕均匀地切割,望远镜正在快速运转着,电脑屏幕前,几个平均年龄不足30岁的工程师正小心翼翼地查看着观测的进展。
观测间隙,当总控室里的前辈、王启明的博士生雷政讲起初入FAST团队的艰辛时,这些年轻的后辈们逐渐靠拢过来,竖起耳朵仔细聆听着,试图通过碎片的讲述拼凑出过去的故事。他们大都是中国科学院大学和贵州大学、贵州师范大学联合培养的硕博毕业生,也是FAST团队中的新生代力量,而对于过去,他们更多的只是听说。
郝巧莉也是这些新生代的力量之一。见到郝巧莉时,她正被其他单位的工作对接人误会,她举着电话认真解释,对方却直接删除了她的微信,她的脸涨得通红。
“成熟”的职场上,郝巧莉此刻或是能收到同事们的安慰,又或是同事们的“假装没看见”,但现实却并非如此。
郝巧莉腾地一声坐在椅子上,办公室里随即爆发出哄堂大笑声。有同事正好刚进门,立马收到别人热情的剧情简介,“你知道么,这么好脾气的郝巧莉居然能被人拉黑!哈哈哈!”
这样的场景仿佛回到了高中课堂,没有虚情假意,也没有冷眼旁观,郝巧莉气着气着也气笑了,大家互相调侃,刚才的不愉快翻篇了。
如果说,最初吸引郝巧莉的是摆放在贵州大学门口的FAST团队的宣传海报,那么现在,最吸引她的无疑是单纯而轻松的工作氛围,几乎每一位接受采访的成员都会提及,“我很喜欢这里的工作氛围。”
或是身着深紫色的、印有FAST标志的工作服,或是身着一身简单的休闲服,没有固定的坐班制度,也没有森严的等级隔阂,每个人都仿佛分工明确的“蚂蚁”穿梭在这座集办公、住宿、休闲和食堂于一体的综合楼里,保证FAST运转系统的正常运行。
“无论我们是哪个系统的,所有人之间都互相认识,关系就是这么铁。”与郝巧莉共同负责科学观测和数据存储与管理工作的黄梦林笑着说,“现场30多个人中只有7个女孩,其中有3个都在这里找到了爱情。”
因为在大山里工作得太久了,人们习惯于把坐班车去贵阳叫“上去”,把回到FAST叫“下来”,透过黄梦林工位旁的窗子向外看,目之所及都是青山绿树。偶然的一次北京出差,刚踏进地铁,她感觉“人太多了,有点恐慌”。
到目前为止,天文学家们观测数据的保存和分发全部都流经于黄梦林和郝巧莉之手。“也不要把我们想象成一心奉献的,虽然是服务FAST的,但我们有自己的职业自豪感,当FAST发现了点什么时,我们觉得与有荣焉。”
晚上10点过后,工作基本告一段落,男子五项(足球、篮球、羽毛球、兵乓球、台球)和女子三项(羽毛球、乒乓球、台球)也偃旗息鼓。
几个加班的同事走进一楼的咖啡厅,熟练地在冰箱里拿出几粒牛肉丸放进烤箱里,而后倒满一杯饮料或是冲泡一杯咖啡,在闲聊中等待着牛肉丸发出滋滋啦啦的声响。
刚刚结束了一场学术报告的咖啡厅里平添了几分烟火气。
未来
从综合楼到大窝凼往返大约需要1万步,王启明熟悉FAST的每条小路。
他的微信签名是“大窝凼”,微信头像则是一张FAST的照片,照片是只有老资历的内行人才知晓的FAST景致。顺着盘旋状的坡道溜达到“锅底”,然后打开手机闪光灯向上仰拍,闪光灯照亮了2225个索网节点上的2225个反光棱镜,于是,碧蓝的夜空下,闪闪点点的是人造的星海。
让人情不自禁想起一句“醉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
目前,FAST的建设工作已经告一段落,但新的挑战接踵而至——望远镜的调试工作。如何能让FAST具备更高的灵敏度,更好地完成任务,这一重担落在了由孙京海、甘恒谦等FAST团队第二代和第三代的中坚力量组成的调试组肩上。
“人是宇宙解释自身的方式”,中国科学院大学天文学院研究生二年级学生殷家宁脱口而出,他也是FAST总工程师姜鹏的学生。
但这句话是怎么出现在他脑子里的,他说不清,“就是一个直觉”。
因为迷恋希腊神话和中国传说中那片瑰丽的星空,殷家宁对天文的兴趣从小就燃起,但爱好者和研究者,并不一样。“爱好者是只爱一个结果,但研究者要了解结果背后的本质。”
本科修读力学,矢志跨专业转到天文学后,殷家宁度过了一个无比充实的研一生活,“把所有能选的和天文有关的课程都选了,度过了一个非常酸爽的考试周——一连五天,上午一门,下午一门。”随后,他再次面临着选择。
在“喜欢星系计算,想成为天文学家”的诱惑面前,殷家宁还是决定先去做一个“支持天文学家”的人,毕竟“支持的是FAST的工作,前无古人,绝无仅有”。目前,殷家宁的研究主要是进行FAST馈源支撑系统的动力学优化,为以后的优化控制做准备。
在其他人看来,殷家宁常呆呆地枯坐在电脑前一动不动,但没人知道,这个男孩正在大脑里进行着一场场艰苦的跋涉,一场场极其消耗心力的思维游戏。他反复自我问询“我的理论模型能不能建成?能不能有用,能不能提高FAST的观测效率?”
同样,他也在不断打破既有认知又不断重建中循环。在深陷迭代法始终无法建模成功许久后,他想,那近似法是不是可以?一试,果然成了!那瞬间,殷家宁称之为“浑浑噩噩里的一点灵光乍现,解脱了”。
“俯视着,像一汪大湖”,殷家宁回想起了第一次见到FAST的情景,“天文学的一切都建立在观测的基础上,而大科学装置就是观测的基础,如果没有它,整个科学前沿无法推进。观测设备的提高,对天文领域都是很重要的问题。”
但殷家宁没有说全的是,FAST影响的可不仅仅是天文领域。
毗邻FAST的克度小镇被媒体称为“被大锅改变的小镇”。FAST观景台、天文体验馆、天文时空塔、天文望远镜形状的路灯和天文科普宣传文化墙……这座被称为“天文小镇”的地方赫然充满着众多科幻与天文的元素。
很难想象,几年以前这里还是一座深居大山的贫困小镇,但在FAST落成一年内,就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24万名游客,旅游业拉动了周边经济,有村民一年的收入翻了7番;旅游业也改变了地方生态,天文学课程第一次出现在孩子们的课表上,与贵州省高校的合作也吸引了人才的回流……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高级工程师、现任平塘县委常委挂职副县长的朱明是联结FAST和地方政府的一条关键“纽带”,他正积极推动当地中小学普及天文基础课程,“这里的民众都感受到了FAST带来的改变,我们也希望,未来这里的孩子们走出去的时候,可以骄傲地告诉别人家乡的‘天眼’究竟是什么。”
深夜11点半,这栋融合了传统吊脚楼特色的现代木质建筑安静下来了。
张博准备回到宿舍休息。综合楼走廊环形连通着,人在各个角度都能被看到,所以人找人也不必铺垫。
“张博,过来看看这是怎么回事。”一位同事从楼上的走道向下探出头来扯着嗓子喊道。
“好嘞,马上!”张博仰着头朝楼上应道,然后噔噔噔踏着楼梯上去……
“我们这个团队,有不能忘记的初心:我们要做一台好用的望远镜!我们有未来美好的愿景:希望后来者们用好这个设备。我们有必须接受的现实:我们是工程团队,尽管工程做得如火如荼,但未来的舞台中心一定属于科学家,我们甘当绿叶,陪衬他们的光辉。但我们还有点奢求:我们希望不会被忘记……”姜鹏在一次演讲中说。
本文原载于《国科大》杂志2019年第3期
原文链接:https://news.ucas.ac.cn/up/2019-3.pdf
责编 :黄巧